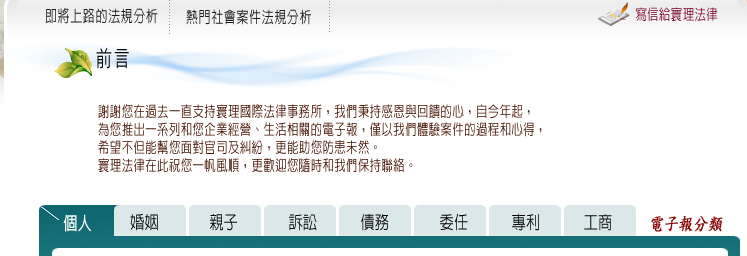不是我
大部分的被告採取的答辯模式,就是否認犯行是自己所為。
無罪推定
所謂無罪推定原則,指的是任何人在被判決確定有罪之前,在法律上都應該視為無罪。這種推定,不指只的是檢察官必須以證據說服法官被告有罪,更強調被告對於自己所涉罪嫌,並沒有任何表示意見或做任何行為的義務。也就是說,被告針對法院或檢警的詢問,可以單純沈默,不回答任何問題,不提出任何證人,然後爭執檢察官的指控實為罪嫌不足。若檢察官無法證明被告的犯罪,則被告就能獲得不起訴處分或無罪判決了。
合理懷疑
檢察官要怎麼樣才能達到說服法官相信被告有罪的標準呢?就是讓法官覺得,被告有罪的程度,已經「超越了合理懷疑」被告無罪的程度。在採行無罪推定的國家,這個標準並不容易達到。實務上,這種課予檢察官舉證的高標準責任,不啻要求法官對於證據的取捨有疑義時,應作有利於被告的認定。從而,被告常常可以爭執,本案對於被告的認定,存在著認定無罪的「合理懷疑」。
不在場抗辯
不在場抗辯,也是無罪答辯常用的方式。在這種答辯中,被告乃是表明自己案發時並不在現場。例如,某甲被指控於星期六下午在基隆某民宅行竊,可能被論以竊盜罪之刑責的情形下,某甲可以找出證人具結作證,證明某甲在當時人並不在基隆,而是在桃園與朋友泡茶聊天。
是我沒錯,但 ….
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縱使檢察官清楚的舉證了被告在本案的行為,被告還是可以躲掉刑責。
正當防衛
在某些被告被指控為傷害案件的類型中,例如以棍棒毆擊、以致命武器攻擊或者殺人等等,正當防衛是一種常常會被提出來使用的防禦方法。也就是說,被告承認確實有檢察官所控訴的行為,但辯稱這是導因於被害人的不法侵害所致。大多數正當防衛的核心議題通常是:
| |
•誰是攻擊者? |
| |
•是否有客觀情況足以使被告相信,被告的防衛行為有正當理由? |
| |
•如果上述的理由是肯定的,那麼被告的行為是否也是合理的? |
正當防衛的理論根基,在於肯定人民可以自行避免生命、身體的不法侵害。換言之,人民不需等到已經遭受攻擊後才採取防衛行為,而是在凡是正常人都會認為將要遭受物理上的攻擊的情況下,就有權利先行採取行動以避免攻擊的發生。不過,採取的行為必須合理適度,否則如果有所逾越,仍然會被認定為防衛過當而遭到刑事處罰。
心神喪失
心神喪失的抗辯,則是奠基於另外一種刑罰理論,也就是只有當人們可以控制自己的行為,而且明白其行為具有可罰性的時候,才應該以刑罰加以處罰。因此,當有些人因心神喪失而導致不能辨別其行為的是非對錯時,即能免於刑責的處罰。
心神喪失理論基礎儘管簡單,卻是一個極為複雜的議題,許多國內外刑法學者對此多有聚訟。
以下是其中兩個重點:
與一般大眾的認知相反,刑事被告其實很少採取心神喪失的抗辯,尤其在有律師擔任辯護人的案件中更是如此。因為,實務上極少有法官願意支持這種抗辯,而讓辯稱行為時心神喪失的被告得以獲判無罪。
在客觀上,到底是否構成心神喪失也是一個極難量化的標準。在我國的司法實務上,被告是否在行為時屬於心神喪失,往往委諸大型教學醫院,例如台大、榮總或林口長庚等單位的專業醫生加以鑑定。然而,與許多涉及專業爭議的問題相同,即使是相同的案件,交由不同的專業醫院鑑定,也不一定能鑑定出相同的結果。
受酒類或藥物影響(原因自由行為)
許多被證實為行為人的被告,往往會以自己受到酒類或藥物的影響,無法自主犯罪時的行為(學說上稱為原因自由行為),以致於不應該為他們的行為付出代價。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於自陷於原因自由行為者,例如在殺人前喝酒壯膽者,則不能免於刑法的追訴。因為一般人都應該知道,酒類或藥物會影響心智的運作,因此凡自陷於此者,即沒有不為其行為負責的道理。
對於某些需要特定意圖的案件,被告可以抗辯,由於酒類或藥物的影響,在行為時完全不具有這樣的特定意圖,因此不構成該需要特定意圖才能成立的犯罪。不過,這種答辯往往並沒有辦法達到完全無罪的效果,而是有可能轉換成不需要該特定意圖才能構成的犯罪。例如,在被告因酒醉而闖入他人家中而擅取他人物品,現場遭人逮獲的案件中,如果檢察官要控告被告竊盜未遂,因為竊盜罪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的特定意圖為成立的前提,該特定意圖即可能因被告酒醉嚴重而難以證明。此時,法官就可能以不需要上開特定意圖的「無故侵入他人住宅」而加以定罪。
陷阱教唆
當政府誘導人民犯罪,並因此而試圖懲罰這種犯罪時,即構成所謂的陷阱教唆。不過,當法官發現被告的犯意並非單純因為警察或其他司法人員的挑唆而產生之時,被告仍然負有刑事責任。例如,在因警方線民而破獲的販毒案件中,被告往往以陷阱教唆而作為答辯的理由。然而,提出這種答辯的被告通常難以證明自己在之前完全沒有販毒的故意,導致最後無法獲得法官的認同。因此,以陷阱教唆答辯的被告,其實也是很難獲得無罪判決的。 |